编者按:近年来,微生物组在不同疾病中作用的相关研究得到广泛开展,并对一些干预策略进行了探索。那么,在肥胖的发生及干预中,微生物组作用如何?在2023 ADA年会上,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Rob Knight博士与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糖尿病中心Max Nieuwdorp博士围绕该话题展开了激烈辩论。
微生物组是肥胖的关键
Knight博士指出,迄今为止,在人类基因组中寻找肥胖发生的关键已花费数十亿美元。那么,我们找对地方了吗?人体内大约有2万个人类基因,但携带的微生物基因却有大约200~2000万个,而这些却是我们常常会忽视的可以改变的基因。
我们可以从人类和微生物基因中建立与健康相关性状的预测模型。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彻底改变了常见性状和疾病基因的发现,包括肥胖相关性状。在不到4年间,52个基因位点被确定与肥胖相关的性状明确相关。然而,目前可用的遗传信息预测能力差,不能准确区分肥胖的高风险与低风险人群。比如,在ARIC研究的8120个个体中计算的32个基因位点的AUCROC与EPIC-Norfolk研究中评估的12个基因位点的AUCROC完全相同(均为0.574),表明额外20个BMI基因位点并没有进一步改善对成人肥胖的遗传预测[1]。而在另一项研究中,经验误差曲线表明,不同的微生物分类单元(OTU)定义可以很好地完成不同的分类任务。比如,根据宿主表型对肠道菌群进行瘦-胖基准的分类,准确度可达90%,16S rRNA序列有82%的同源性[2]。
2018年发表在Nature上的一项研究[3]分析了1046例健康个体的基因型和微生物组数据,这些个体有着不同的祖先来源,共享相对共同的环境,证明微生物组与遗传祖先没有显著关联,宿主遗传学在决定微生物组组成方面起次要作用。相比之下,在共同居住的家庭环境下,个体微生物组组成有显著相似性,超过20%的个体间微生物组变异性与饮食、药物和人体测量相关因素有关。研究进一步证明,与仅使用宿主遗传和环境数据的模型相比,微生物组数据显著提高了许多人类性状的预测准确性,如葡萄糖和肥胖指标
不仅仅是肥胖,在动物研究中发现微生物组在炎症性肠病、结肠癌、帕金森病、多发性硬化症、自闭症等的发生中也发挥了作用,但很多研究仍为观察性的,还需证明其机制以及明确哪些特定的微生物和代谢物参与其中。通过粪菌移植(FMT)可以治疗或引发小鼠的许多疾病。那么,FMT能治愈人类肥胖吗?Knight博士展示了FMT在真正有效情况下的表现。他举例,当将1例健康人的肠道菌群通过FMT用于4例肥胖患者时,在短短两三天内,他们的肠道菌群从不健康状态恢复到健康状态,同时临床症状消失。但是,FMT效果是否有限制呢?他打个比方,有只狗很喜欢看天鹅,希望自己也能飞,就经常食用天鹅的粪便,但却从未学会飞,这只是它的幻想而已。所以,想要用FMT来实现一些不切实际的效果是不现实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
Knight博士提到,饮食与肥胖有关,这是毋庸置疑的。正如精准生活方式医学研究所负责人Jeff Bland所讲,“食物是一种与我们基因对话的语言”。但是,它表达的方式却千差万别,这取决于我们吃的食物。理解这种语言对于解决肥胖问题至关重要。比如,一项前瞻性研究[4]纳入3个独立队列120 877例基线无慢性疾病且不肥胖的受试者,每隔4年评估一次生活方式因素变化与体重变化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特定的饮食和生活方式因素与长期体重增加独立相关,具有显著的累积效应。而且,人们对饮食的反应存在个体差异。发表在Cell上的一项研究[5]对800例健康成人进行为期1周的血糖监测,分析46 898餐的反应,发现吃同样食物的人在餐后血糖反应方面差异很大。结合饮食习惯、体力活动和肠道菌群等参数能够准确预测血糖反应,个体化饮食可能会成功降低餐后血糖及其长期代谢结局。
微生物组导向的癌症干预已经在挽救患者的生命。肠道细菌可调节癌症患者对免疫检查点阻断(ICB)治疗的应答,但饮食和补充剂对这种相互作用的影响尚未经过充分研究。一项研究[6]在黑色素瘤患者中评估了粪便微生物群特征、饮食习惯和市售益生菌补充剂的使用情况,并进行平行的临床前研究。结果发现,在128例接受ICB治疗的患者中,较高膳食纤维与无进展生存期显著改善相关,在膳食纤维摄入充足且未使用益生菌的患者中观察到的获益最显著。临床前模型研究也得到同样结果——在接受低纤维饮食或益生菌的小鼠中,基于抗PD-1疗法的治疗应答受损,并且肿瘤微环境中干扰素-γ阳性细胞毒性T细胞的频率较低。可见,尽管纤维对患者有益,但补充益生菌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Knight博士指出,真正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为微生物群建立一个用户界面。现在很难通过数据来告诉患者应该怎么做。也许未来会发明一种智能马桶,只要冲水就会把粪便中的微生物群样本数据传送到智能手机上,帮助人们跟踪其变化趋势,并采取相应饮食干预。以此类推,对于琳琅满目的食物,未来也许可通过智能扫描分析判断其对体重的影响来决定摄入与否以及摄入量。这也是圣地亚哥微生物组创新中心正在做的疯狂的事情。所以,Knight博士认为微生物组是肥胖的关键,但必须用这把钥匙打开正确的门。
微生物组在肥胖中的作用纯属炒作
Nieuwdorp博士介绍,自2004年第一篇文章[7]发表以来,关于肠道菌群与肥胖的相关研究激增,其中大多数是在小鼠中开展的。在Sender R等人的研究[8]中,以体重70 kg的成人男性为例,估计了人体中不同细胞类型的细胞数量和质量分布。从中可见,在细胞数量上,细菌的数量(3.8×1013)超出人体主要组织细胞(3.0×1013)的总和;但在质量上,细菌仅为0.2 kg,约占体重的0.3%。
虽然人体是“行走的微生物群落”,但这与体重和代谢有关吗?Nieuwdorp博士认为,这就像“房间里的大象”,他结合3个关键问题进行了分析。
01效应大小的外推:小鼠与人类不同
在饮食对总体菌群变化的影响方面,在小鼠研究中,饮食变化可解释57%[9]或61%[10]的肠道菌群结构变化,在塑造肠道菌群方面起着主导作用[11];而在人类研究中,根据17例欧洲人的宏基因组研究,饮食仅能解释5%的肠道菌群变化[12],而且个体差异较大。由于小鼠之间的基因更相似,干预比人类研究更极端,其饮食受到严格控制,且与人类的肠道宏基因组共享的相同基因比例极低。因此,在小鼠中开展的研究并不能很好地外推到人类中。
此外,饮食对人类肠道菌群的影响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一项有关饮食干预调节肠道菌群和心血管代谢疾病(CMD)的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13]纳入了15项随机对照试验和6项非随机临床试验。在所有研究中,总体偏倚风险都很高。总的来说,大多数饮食干预改变了肠道菌群组成,但未发现一致的影响。
02观察性肠道菌群研究的可重复性
多项研究表明,代谢综合征和2型糖尿病的发生与肠道菌群组成改变相关[14-16]。那么,这些数据的可重复性如何?当汇集这些研究(以期增加效力)时,证实了消瘦和肥胖受试者在菌门水平分类组成上的差异,但BMI与肠道菌群分类学组成之间无相关性[17]。研究之间的差异可能是由于饮食、种族或其他混杂因素如药物使用的差异导致的。在这方面,Falcony等人估计,每项研究需要1700多例受试者的样本量才能充分评估这种关系[18]。
包括荷兰多种族HELIUS队列研究、亚马逊土著居民研究均表明了种族多样性对肠道菌群的影响。其中,在亚马逊土著居民研究中,粪便菌群多样性在几代内消失了。与亚马逊土著居民的传统饮食相比,美国西方饮食者的粪便菌群多样性约减少30%[19]。HELIUS研究[20]发现,生活在同一城市的个体往往与其共同种族背景的人具有相似的肠道菌群特征。荷兰人的肠道菌群α-多样性最大,南亚苏里南人的α-多样性最小,存在相应的OTU富集或缺失。因此,个体的种族起源可能是微生物组研究及其在种族多样化社会中潜在未来应用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甚至有研究发现,同居的家庭成员彼此之间以及与他们的宠物狗之间会共享肠道菌群[21]。HELIUS研究还发现,肠道菌群与宿主基因型的关联因种族而异,并可能影响心血管代谢特征[22]。
对于糖尿病来说,有多种方法进行诊断,比如HbA1c、空腹血糖、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且有相应的参考范围,并需要次日重复检测来确诊。然而,对于肠道菌群来说,目前并没有正常或异常的标准化参考值。
03因果关系 vs. 相关性
人类代谢性疾病中细菌与疾病因果关系的科赫假设为:必须从患病器官中鉴定/分离出微生物,微生物应与人类疾病相关(关联/干预),引入的微生物应能够复制表型(接种)。
来自美国肠道项目10 534例参与者的研究[23]数据表明,Akkermansia基因相对丰度高与肥胖风险低相关,且随年龄增长相关性降低。另一项在超重/肥胖的胰岛素抵抗志愿者中进行的初步研究[24]发现,与安慰剂组相比,每日口服补充1010个Akkermansia mucinophilia 3个月后,胰岛素敏感性、胰岛素血症、血浆总胆固醇等代谢指标均得到显著改善。
在针对肠道菌群的其他干预方面,FMT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近年来,科学研究一直在寻找FMT作为一种有希望的治疗多种疾病的方法。FMT治疗代谢综合征已被证明是一种研究肠道菌群作用的有趣方法,并通过解析微生物群驱动的胰岛素抵抗为新疗法开辟了道路[25]。然而,在目前FMT及其对人类肥胖影响的研究中,未发现供体FMT对BMI/体重有影响,但有3项研究发现FMT对胰岛素抵抗和胆固醇产生有益影响;1项自体FMT研究显示对胰岛素抵抗的有益作用(在6个月的饮食干预后给予)。
Nieuwdorp博士最后总结指出,目前已发表的观察性研究在样本量、种族、饮食影响等方面存在偏倚;技术方面也存在问题,比如没有微生物组的参考值,也没有标准化的生物信息学技术;而且,研究发现的相关性并不等同于因果关系;有关细菌菌株或FMT的干预性研究未显示对体重/BMI有影响,但可能对胰岛素抵抗有影响;从肥胖(而非胰岛素抵抗)的角度来看,微生物组迄今为止仍是一种炒作。
参考文献
1. Loos RJ. Best Pract Res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12; 26(2): 211-226.
2. Knights D, et al. Cell Host Microbe. 2011; 10(4): 292-296.
3. Rothschild D, et al. Nature. 2018; 555(7695): 210-215.
4. Mozaffarian D, et al. N Engl J Med. 2011; 364(25): 2392-2404.
5. Zeevi D, et al. Cell. 2015; 163(5): 1079-1094.
6. Spencer CN, et al. Science. 2021; 374(6575): 1632-1640.
7. Bckhed F, et al.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04; 101(44): 15718-15723.
8. Sender R, et al. PLoS Biol. 2016; 14(8): e1002533.
9. Zhang C, et al. ISME J. 2010; 4(2): 232-241.
10. Faith JJ, et al. Science. 2011; 333(6038): 101-104.
11. Hildebrandt MA, et al. Gastroenterology. 2009; 137(5): 1716-24. e1-2.
12. Tap J, et al. Environ Microbiol. 2009; 11(10): 2574-2584.
13. Attaye I, et al. Gastroenterology. 2022; 162(7): 1911-1932.
14. Qin J, et al. Nature. 2012; 490(7418): 55-60.
15. Le Chatelier E, et al. Nature. 2013; 500(7464): 541-546.
16. Karlsson FH, et al. Nature. 2013; 498(7452): 99-103.
17. Finucane MM, et al. PLoS One. 2014; 9(1): e84689.
18. Falony G, et al. Science. 2016; 352(6285): 560-564.
19. Clemente JC, et al. Sci Adv. 2015; 1(3): e1500183.
20. Deschasaux M, et al. Nat Med. 2018; 24(10): 1526-1531.
21. Song SJ, et al. Elife. 2013; 2: e00458.
22. Boulund U, et al. Cell Host Microbe. 2022; 30(10): 1464-1480.e6.
23. Zhou Q, et al. Nutr Metab (Lond). 2020; 17: 90.
24. Depommier C, et al. Nat Med. 2019; 25(7): 1096-1103.
25. de Groot PF, et al. Gut Microbes. 2017; 8(3): 253-267.
声明:本文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了解最新医药资讯参考使用,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该等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果该信息被用于资讯以外的目的,本站及作者不承担相关责任。
2 comm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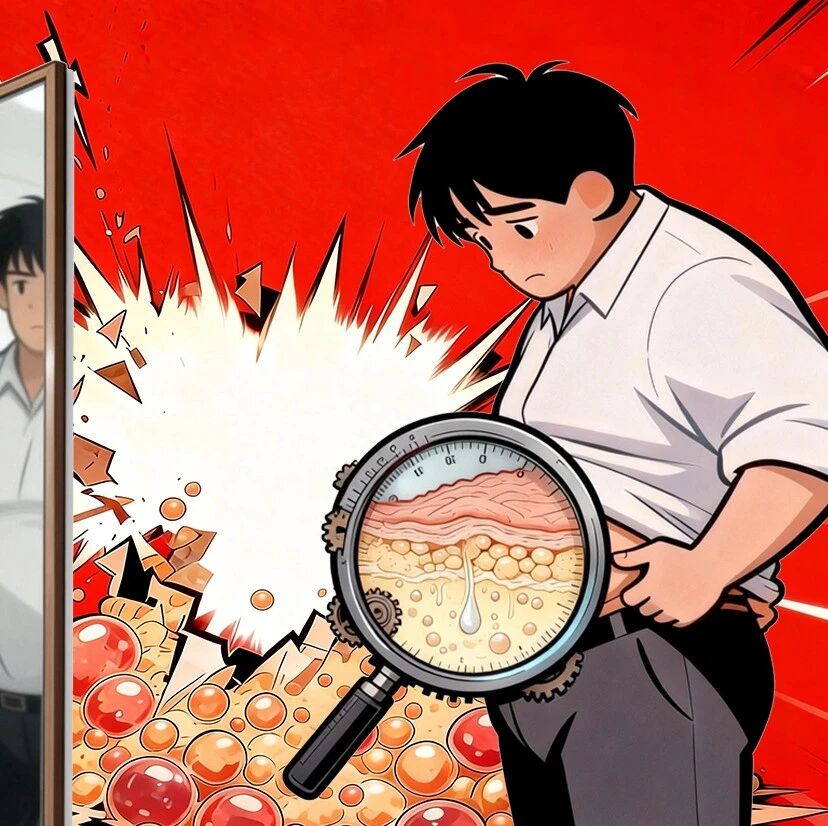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336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3361号
发布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