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5年6月22日,第85届美国糖尿病协会科学年会(ADA 2025)上,一场题为“当2型糖尿病(T2DM)治疗变得微妙”的专题研讨引发关注,4位专家聚焦瘦型T2DM、酮症倾向型糖尿病(KPD)、终末期肝病(ESLD)合并T2DM、终末期肾病(ESKD)合并T2DM四类“非典型”人群,系统阐述其特殊病理机制、治疗陷阱及应对策略,展现了糖尿病治疗从“控制数值”向“整合个体代谢状态”转变的趋势。本文整理四位讲者的详细内容与治疗建议,助力医生更好地识别边缘患者、规避治疗陷阱、实现代谢平衡。
瘦型T2DM患者——警惕“体重正常”的代谢误导

Kristina Utzschneider
弗吉尼亚普吉特湾医疗保健系统和华盛顿大学医学系代谢、内分泌和营养部Kristina Utzschneider博士讲到,瘦型T2DM在临床中日益受到关注,尤其在亚洲人群中更为常见。尽管传统医学教科书通常将T2DM定义为胰岛素抵抗基础上的胰岛素分泌不足,多见于超重或肥胖个体,但现实中不少患者体型瘦削,体重指数(BMI)正常或偏低。Utzschneider博士强调,对于这类“瘦体型”T2DM患者,首先应重新审视诊断基础,重点排除自身免疫性糖尿病(如T1DM、LADA)、基因相关糖尿病(MODY)、线粒体糖尿病、胰腺源性糖尿病及其他罕见类型。这种“排除诊断”过程要求临床医生具备更高的鉴别能力,避免误诊。瘦型T2DM的定义在非亚洲人群为BMI<25 kg/m2,亚洲人群为BMI<22 kg/m2。值得注意的是,瘦体型并不等同于胰岛素敏感性高,肥胖也不必然代表胰岛素抵抗。BMI作为体型评估指标存在局限,部分瘦人群内脏脂肪及异位脂肪含量较高,代谢风险并不低;反之,部分高BMI者可能肌肉发达,代谢状况良好。
瘦体型T2DM的发病机制主要以β细胞功能障碍为主,患者胰岛素分泌能力不足,难以维持正常血糖水平,胰岛素敏感性则相对较好。多项流行病学研究显示,瘦体型T2DM并不罕见,美国NHANES数据中BMI<25 kg/m2的患者占10.2%,韩国类似人群(BMI 18.5~22.9 kg/m2)比例达23.3%。不同族裔的BMI阈值存在差异,南亚人群在BMI仅19~20 kg/m2时发病风险即显著升高,远低于白人。这揭示了亚裔人群在代谢敏感性和胰岛功能方面存在的独特缺陷。Utzschneider博士分享的临床研究表明,低热量饮食(VLCD)干预对瘦体型患者同样有效,70%的患者在饮食调整后实现糖尿病缓解,平均体重仅下降6.5%,这表明,通过优化内脏脂肪分布、增强胰岛功能及提高胰岛素敏感性,瘦体型T2DM患者同样有望实现病情的有效控制乃至逆转。
在治疗策略上,虽然尚无明确指南依据BMI调整用药,但BMI与C肽水平等指标可为个体化治疗提供参考。C肽反映胰岛素分泌能力,低于0.6 ng/ml可能提示需胰岛素治疗,而高于2.7 ng/ml可优先考虑口服药物,但其检测受多种因素影响,需结合临床判断。Utzschneider博士强调,当前针对瘦体型T2DM的研究尚显不足,未来亟需借助大数据和多组学技术,构建更为精准的分类与预测模型,以患者个体差异为导向,推动精准医疗的发展。总之,瘦体型T2DM作为被低估的临床亚型,不应因“瘦”而轻视其风险,精准诊断和个体化管理是提升患者预后和治疗效果的关键。
酮症倾向型糖尿病——隐藏在DKA背后的T2DM亚型

Priya Vellanki
美国埃默里大学医学院内分泌学系Priya Vellanki博士以一例58岁非裔美国男性的典型病例为切入点,介绍了该患者因酮症酸中毒入院,经过胰岛素强化治疗后,3个月内成功停用胰岛素,并在1年内维持良好血糖控制,空腹C肽水平明显恢复。这一病例凸显了KPDM独特的病理生理特点——起病时呈胰岛素依赖状态,但β细胞功能具备显著的可逆性,区别于传统1型糖尿病(T1DM)中不可逆的β细胞衰竭。
Vellanki博士强调,KPDM在非裔及西班牙裔人群中较为普遍,且男性患者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女性。患者多以无诱因的酮症酸中毒或严重高血糖发作为首发症状,伴随肥胖及胰岛素抵抗,且自身抗体多为阴性。她进一步介绍了KPDM的4种分型方法,强调抗体阴性且β细胞功能保留型最为常见。与T1DM和T2DM相比,KPDM在临床表现和发病机制方面均呈现出独特的双重性质。
在发病机制方面,Vellanki博士强调胰岛素抵抗与肝脏酮体代谢异常共同驱动了KPDM的酮症状态。患者初期存在严重胰岛素抵抗,β细胞处于代偿性负荷状态,短暂功能抑制伴随线粒体氧化酮体能力下降,导致β-羟基丁酸水平显著升高。她指出,这一机制区别于传统糖尿病酮症,提示KPDM可能涉及独特的线粒体功能异常。
关于治疗策略,Vellanki博士强调急性期应严格遵循酮症酸中毒治疗规范,缓解期逐步减少胰岛素用量,联合二甲双胍或二肽基肽酶4抑制剂(DPP-4i)等口服药物,以降低复发风险并维持血糖稳定。长期随访显示,尽管DKA复发率较高,但大部分患者复发后仍可恢复胰岛素独立性,提示动态监测与个体化管理的重要性。
最后,Vellanki博士提到,KPDM是否为独立疾病实体尚存争议,但其独特的临床表现和遗传背景可能为糖尿病的精准诊疗提供新的思路。未来研究需聚焦于分子机制解析、生物标志物开发及个体化治疗策略,以完善KPDM的诊断与管理体系,提升患者预后。
终末期肝病合并T2DM——在多重代谢失衡中寻找稳态路径

Thomas Jensen
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Thomas Jensen博士指出,T2DM在ESLD患者中极为常见,整体患病率可达32%,在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相关ESLD患者中更高达56%。这一流行病学趋势的背后,是“代谢-肝脏”之间不断强化的病理循环——胰岛素抵抗、肝细胞功能衰退与炎症反应共同作用,导致T2DM加重肝纤维化,肝功能恶化又反过来加剧高血糖。在这种双向驱动的机制中,肥胖、慢性炎症、糖脂毒性以及肝脏胰岛素清除障碍相互交织,极大加重患者综合疾病负担。
在血糖监测方面,Jensen博士强调,传统的HbA1c在ESLD患者中常被低估,其替代指标如果糖胺、糖化白蛋白虽更敏感,但仍受低蛋白血症等因素干扰。他建议结合OGTT和持续葡萄糖监测(CGM),并根据Child-Pugh分级调整评估频率,尤其在Child B/C期需警惕低血糖与肝性脑病风险。
针对药物治疗策略,Jensen博士提出,药物选择必须建立在“肝功能评估+个体代谢需求”双重基础上。例如,他汀类中,瑞舒伐他汀、普伐他汀和匹伐他汀在Child A/B期患者中相对安全,Child C期则需权衡风险;二甲双胍适用于Child A期,Child B期需谨慎,eGFR<30 ml/min时禁用;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在Child B期中慎用,Child C期中不推荐;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在改善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MASH)和心血管风险方面潜力巨大,Child C期患者使用前需综合评估营养与炎症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非药物干预在管理策略中同样占据重要地位。Jensen博士强调,营养支持和抗阻运动可改善肌少症、减少门静脉高压;体重减轻5%~10%即可获得明显临床获益。而对于代偿期患者,减重手术如袖状胃切除术可在严密评估后安全实施,失代偿期则需极度谨慎。展望未来,Jensen博士介绍了多个正在进行的新型治疗方向,包括GLP-1/SGLT2双靶点药物、非他汀类调脂药(如bempedoic acid)、肝-胰联合移植与代谢手术的序贯方案等。这些策略正逐步推动ESLD与T2DM共病管理从经验医学迈向精准医学时代。
Jensen博士总结道,ESLD与T2DM共病管理是当前代谢医学与肝病领域的重要交汇点。临床工作中需在血糖控制、肝功能保护与多系统协作之间保持动态平衡,推动个体化治疗决策,并期待未来有更多高质量循证研究为实践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透析患者中的T2DM——控糖不是目标,避免伤害才是底线

Jeffrey Berns
宾夕法尼亚大学Jeffrey Berns博士表示,透析患者合并T2DM管理是一个“最不标准化”的领域。在ESKD患者中,传统HbA1c用于评估血糖控制面临诸多限制,如贫血、输血及促红细胞生成素使用等因素均可导致HbA1c低估真实血糖水平。因此,根据KDIGO指南,当HbA1c与临床表现或指尖血糖不一致时,推荐优先使用CGM或自我血糖监测(SMBG),以获取更准确的血糖管理数据。此外,不同透析方式也会影响血糖波动特征:腹膜透析(PD)患者因透析液中葡萄糖吸收更易高血糖,而血液透析(HD)患者则常在透析过程中出现低血糖,需特别警惕。
面对ESKD患者复杂的代谢状态,Berns博士强调个体化血糖控制目标的重要性。对多数患者而言,HbA1c控制在7.0%~8.0%是相对安全的范围,同时结合葡萄糖目标范围内时间(TIR)(建议目标50%~70%)进行动态评估。年轻、合并症少的患者可尝试更严格控制,高龄、有认知障碍或预期寿命有限者则应优先避免低血糖风险,适当放宽目标。
在HD和PD患者中,目前尚无关于胰岛素与口服降糖药优先使用的统一共识。只要能够实现并维持良好的血糖控制,同时避免低血糖事件,胰岛素和口服药均可作为可接受的治疗选择。然而,鉴于透析患者使用胰岛素时低血糖风险较高,临床上需格外谨慎。
关于胰岛素治疗,其仍是ESKD合并T2DM管理的基础药物,但需调整剂量和方案。慢性肾脏病(CKD)患者使用胰岛素的基本原则与非CKD患者相似,但目前尚缺乏针对胰岛素种类的具体指南。一般建议从非CKD剂量的50%起始用量开始,且在透析日减少25%~50%。由于HD患者的每日进食量波动较大,若不需要使用基础胰岛素,优先考虑餐时速效胰岛素。大多数合并糖尿病的PD患者最终需胰岛素治疗。尽管在透析方式转换时缺乏明确的指导数据,但临床观察仍揭示PD阶段血糖普遍偏高,HD阶段则面临更显著的低血糖风险。
在口服降糖药方面,需优先考虑安全性。磺脲类中可选用小剂量格列吡嗪,应慎用格列美脲;二甲双胍因乳酸酸中毒风险,在ESKD中禁用。DPP-4i部分药物可用,但需调整剂量,部分需在透析后补剂。总体而言,使用口服药时必须严格评估患者的肾功能状况及低血糖风险。
Berns博士还简要提及GLP-1RA在ESKD人群中的潜在益处。一项队列研究提示,其可能带来全因死亡率下降与移植等待机会提升,同时具备一定的减重效果,适合BMI较高、目标为肾移植的患者。起始剂量应保守,逐步滴定,同时注意其潜在的胃肠不良反应。至于SGLT2i,目前研究主要聚焦其心血管保护作用,在透析患者中使用仍需谨慎,尤其是无尿患者应警惕酮症酸中毒风险。
总结而言,血糖控制目标方面,HbA1c在ESKD患者中的指导意义有限,缺乏充分证据显示其与临床结局的强相关性,但HbA1c>8%时心血管事件及死亡风险明显升高。相较于其他方法,CGM对该人群或许更为适宜,只是其普及程度尚显不足。治疗选择上,倾向优先使用胰岛素,建议以较低剂量起始,并首选胰岛素类似物替代人胰岛素;口服药则可考虑格列吡嗪或DPP-4i。GLP-1RA和SGLT2i在透析患者中应用尚处于探索阶段,可能在心血管保护及移植前体重管理中具有潜力,需更多临床数据支持。Berns博士呼吁,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透析患者的个体化血糖目标和长期结局,以构建更安全、有效的治疗策略。
结语
本场专题展示了当代糖尿病治疗的一个趋势转变——从“疾病导向”走向“个体导向”,这四类人群虽表现形式不同,但共同点在于无法被传统指南充分覆盖。医生需要识别“糖尿病谱系”背后的异质性,理解每例患者的代谢状态、器官功能、社会支持与生活目标,并据此制定动态调整的治疗方案。
2 comments
2025年6月22日,第85届美国糖尿病协会科学年会(ADA 2025)上,一场题为“当2型糖尿病(T2DM)治疗变得微妙”的专题研讨引发关注,4位专家聚焦瘦型T2DM、酮症倾向型糖尿病(KPD)、终末期肝病(ESLD)合并T2DM、终末期肾病(ESKD)合并T2DM四类“非典型”人群,系统阐述其特殊病理机制、治疗陷阱及应对策略,展现了糖尿病治疗从“控制数值”向“整合个体代谢状态”转变的趋势。本文整理四位讲者的详细内容与治疗建议,助力医生更好地识别边缘患者、规避治疗陷阱、实现代谢平衡。
瘦型T2DM患者——警惕“体重正常”的代谢误导

Kristina Utzschneider
弗吉尼亚普吉特湾医疗保健系统和华盛顿大学医学系代谢、内分泌和营养部Kristina Utzschneider博士讲到,瘦型T2DM在临床中日益受到关注,尤其在亚洲人群中更为常见。尽管传统医学教科书通常将T2DM定义为胰岛素抵抗基础上的胰岛素分泌不足,多见于超重或肥胖个体,但现实中不少患者体型瘦削,体重指数(BMI)正常或偏低。Utzschneider博士强调,对于这类“瘦体型”T2DM患者,首先应重新审视诊断基础,重点排除自身免疫性糖尿病(如T1DM、LADA)、基因相关糖尿病(MODY)、线粒体糖尿病、胰腺源性糖尿病及其他罕见类型。这种“排除诊断”过程要求临床医生具备更高的鉴别能力,避免误诊。瘦型T2DM的定义在非亚洲人群为BMI<25 kg/m2,亚洲人群为BMI<22 kg/m2。值得注意的是,瘦体型并不等同于胰岛素敏感性高,肥胖也不必然代表胰岛素抵抗。BMI作为体型评估指标存在局限,部分瘦人群内脏脂肪及异位脂肪含量较高,代谢风险并不低;反之,部分高BMI者可能肌肉发达,代谢状况良好。
瘦体型T2DM的发病机制主要以β细胞功能障碍为主,患者胰岛素分泌能力不足,难以维持正常血糖水平,胰岛素敏感性则相对较好。多项流行病学研究显示,瘦体型T2DM并不罕见,美国NHANES数据中BMI<25 kg/m2的患者占10.2%,韩国类似人群(BMI 18.5~22.9 kg/m2)比例达23.3%。不同族裔的BMI阈值存在差异,南亚人群在BMI仅19~20 kg/m2时发病风险即显著升高,远低于白人。这揭示了亚裔人群在代谢敏感性和胰岛功能方面存在的独特缺陷。Utzschneider博士分享的临床研究表明,低热量饮食(VLCD)干预对瘦体型患者同样有效,70%的患者在饮食调整后实现糖尿病缓解,平均体重仅下降6.5%,这表明,通过优化内脏脂肪分布、增强胰岛功能及提高胰岛素敏感性,瘦体型T2DM患者同样有望实现病情的有效控制乃至逆转。
在治疗策略上,虽然尚无明确指南依据BMI调整用药,但BMI与C肽水平等指标可为个体化治疗提供参考。C肽反映胰岛素分泌能力,低于0.6 ng/ml可能提示需胰岛素治疗,而高于2.7 ng/ml可优先考虑口服药物,但其检测受多种因素影响,需结合临床判断。Utzschneider博士强调,当前针对瘦体型T2DM的研究尚显不足,未来亟需借助大数据和多组学技术,构建更为精准的分类与预测模型,以患者个体差异为导向,推动精准医疗的发展。总之,瘦体型T2DM作为被低估的临床亚型,不应因“瘦”而轻视其风险,精准诊断和个体化管理是提升患者预后和治疗效果的关键。
酮症倾向型糖尿病——隐藏在DKA背后的T2DM亚型

Priya Vellanki
美国埃默里大学医学院内分泌学系Priya Vellanki博士以一例58岁非裔美国男性的典型病例为切入点,介绍了该患者因酮症酸中毒入院,经过胰岛素强化治疗后,3个月内成功停用胰岛素,并在1年内维持良好血糖控制,空腹C肽水平明显恢复。这一病例凸显了KPDM独特的病理生理特点——起病时呈胰岛素依赖状态,但β细胞功能具备显著的可逆性,区别于传统1型糖尿病(T1DM)中不可逆的β细胞衰竭。
Vellanki博士强调,KPDM在非裔及西班牙裔人群中较为普遍,且男性患者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女性。患者多以无诱因的酮症酸中毒或严重高血糖发作为首发症状,伴随肥胖及胰岛素抵抗,且自身抗体多为阴性。她进一步介绍了KPDM的4种分型方法,强调抗体阴性且β细胞功能保留型最为常见。与T1DM和T2DM相比,KPDM在临床表现和发病机制方面均呈现出独特的双重性质。
在发病机制方面,Vellanki博士强调胰岛素抵抗与肝脏酮体代谢异常共同驱动了KPDM的酮症状态。患者初期存在严重胰岛素抵抗,β细胞处于代偿性负荷状态,短暂功能抑制伴随线粒体氧化酮体能力下降,导致β-羟基丁酸水平显著升高。她指出,这一机制区别于传统糖尿病酮症,提示KPDM可能涉及独特的线粒体功能异常。
关于治疗策略,Vellanki博士强调急性期应严格遵循酮症酸中毒治疗规范,缓解期逐步减少胰岛素用量,联合二甲双胍或二肽基肽酶4抑制剂(DPP-4i)等口服药物,以降低复发风险并维持血糖稳定。长期随访显示,尽管DKA复发率较高,但大部分患者复发后仍可恢复胰岛素独立性,提示动态监测与个体化管理的重要性。
最后,Vellanki博士提到,KPDM是否为独立疾病实体尚存争议,但其独特的临床表现和遗传背景可能为糖尿病的精准诊疗提供新的思路。未来研究需聚焦于分子机制解析、生物标志物开发及个体化治疗策略,以完善KPDM的诊断与管理体系,提升患者预后。
终末期肝病合并T2DM——在多重代谢失衡中寻找稳态路径

Thomas Jensen
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Thomas Jensen博士指出,T2DM在ESLD患者中极为常见,整体患病率可达32%,在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相关ESLD患者中更高达56%。这一流行病学趋势的背后,是“代谢-肝脏”之间不断强化的病理循环——胰岛素抵抗、肝细胞功能衰退与炎症反应共同作用,导致T2DM加重肝纤维化,肝功能恶化又反过来加剧高血糖。在这种双向驱动的机制中,肥胖、慢性炎症、糖脂毒性以及肝脏胰岛素清除障碍相互交织,极大加重患者综合疾病负担。
在血糖监测方面,Jensen博士强调,传统的HbA1c在ESLD患者中常被低估,其替代指标如果糖胺、糖化白蛋白虽更敏感,但仍受低蛋白血症等因素干扰。他建议结合OGTT和持续葡萄糖监测(CGM),并根据Child-Pugh分级调整评估频率,尤其在Child B/C期需警惕低血糖与肝性脑病风险。
针对药物治疗策略,Jensen博士提出,药物选择必须建立在“肝功能评估+个体代谢需求”双重基础上。例如,他汀类中,瑞舒伐他汀、普伐他汀和匹伐他汀在Child A/B期患者中相对安全,Child C期则需权衡风险;二甲双胍适用于Child A期,Child B期需谨慎,eGFR<30 ml/min时禁用;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在Child B期中慎用,Child C期中不推荐;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在改善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MASH)和心血管风险方面潜力巨大,Child C期患者使用前需综合评估营养与炎症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非药物干预在管理策略中同样占据重要地位。Jensen博士强调,营养支持和抗阻运动可改善肌少症、减少门静脉高压;体重减轻5%~10%即可获得明显临床获益。而对于代偿期患者,减重手术如袖状胃切除术可在严密评估后安全实施,失代偿期则需极度谨慎。展望未来,Jensen博士介绍了多个正在进行的新型治疗方向,包括GLP-1/SGLT2双靶点药物、非他汀类调脂药(如bempedoic acid)、肝-胰联合移植与代谢手术的序贯方案等。这些策略正逐步推动ESLD与T2DM共病管理从经验医学迈向精准医学时代。
Jensen博士总结道,ESLD与T2DM共病管理是当前代谢医学与肝病领域的重要交汇点。临床工作中需在血糖控制、肝功能保护与多系统协作之间保持动态平衡,推动个体化治疗决策,并期待未来有更多高质量循证研究为实践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透析患者中的T2DM——控糖不是目标,避免伤害才是底线

Jeffrey Berns
宾夕法尼亚大学Jeffrey Berns博士表示,透析患者合并T2DM管理是一个“最不标准化”的领域。在ESKD患者中,传统HbA1c用于评估血糖控制面临诸多限制,如贫血、输血及促红细胞生成素使用等因素均可导致HbA1c低估真实血糖水平。因此,根据KDIGO指南,当HbA1c与临床表现或指尖血糖不一致时,推荐优先使用CGM或自我血糖监测(SMBG),以获取更准确的血糖管理数据。此外,不同透析方式也会影响血糖波动特征:腹膜透析(PD)患者因透析液中葡萄糖吸收更易高血糖,而血液透析(HD)患者则常在透析过程中出现低血糖,需特别警惕。
面对ESKD患者复杂的代谢状态,Berns博士强调个体化血糖控制目标的重要性。对多数患者而言,HbA1c控制在7.0%~8.0%是相对安全的范围,同时结合葡萄糖目标范围内时间(TIR)(建议目标50%~70%)进行动态评估。年轻、合并症少的患者可尝试更严格控制,高龄、有认知障碍或预期寿命有限者则应优先避免低血糖风险,适当放宽目标。
在HD和PD患者中,目前尚无关于胰岛素与口服降糖药优先使用的统一共识。只要能够实现并维持良好的血糖控制,同时避免低血糖事件,胰岛素和口服药均可作为可接受的治疗选择。然而,鉴于透析患者使用胰岛素时低血糖风险较高,临床上需格外谨慎。
关于胰岛素治疗,其仍是ESKD合并T2DM管理的基础药物,但需调整剂量和方案。慢性肾脏病(CKD)患者使用胰岛素的基本原则与非CKD患者相似,但目前尚缺乏针对胰岛素种类的具体指南。一般建议从非CKD剂量的50%起始用量开始,且在透析日减少25%~50%。由于HD患者的每日进食量波动较大,若不需要使用基础胰岛素,优先考虑餐时速效胰岛素。大多数合并糖尿病的PD患者最终需胰岛素治疗。尽管在透析方式转换时缺乏明确的指导数据,但临床观察仍揭示PD阶段血糖普遍偏高,HD阶段则面临更显著的低血糖风险。
在口服降糖药方面,需优先考虑安全性。磺脲类中可选用小剂量格列吡嗪,应慎用格列美脲;二甲双胍因乳酸酸中毒风险,在ESKD中禁用。DPP-4i部分药物可用,但需调整剂量,部分需在透析后补剂。总体而言,使用口服药时必须严格评估患者的肾功能状况及低血糖风险。
Berns博士还简要提及GLP-1RA在ESKD人群中的潜在益处。一项队列研究提示,其可能带来全因死亡率下降与移植等待机会提升,同时具备一定的减重效果,适合BMI较高、目标为肾移植的患者。起始剂量应保守,逐步滴定,同时注意其潜在的胃肠不良反应。至于SGLT2i,目前研究主要聚焦其心血管保护作用,在透析患者中使用仍需谨慎,尤其是无尿患者应警惕酮症酸中毒风险。
总结而言,血糖控制目标方面,HbA1c在ESKD患者中的指导意义有限,缺乏充分证据显示其与临床结局的强相关性,但HbA1c>8%时心血管事件及死亡风险明显升高。相较于其他方法,CGM对该人群或许更为适宜,只是其普及程度尚显不足。治疗选择上,倾向优先使用胰岛素,建议以较低剂量起始,并首选胰岛素类似物替代人胰岛素;口服药则可考虑格列吡嗪或DPP-4i。GLP-1RA和SGLT2i在透析患者中应用尚处于探索阶段,可能在心血管保护及移植前体重管理中具有潜力,需更多临床数据支持。Berns博士呼吁,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透析患者的个体化血糖目标和长期结局,以构建更安全、有效的治疗策略。
结语
本场专题展示了当代糖尿病治疗的一个趋势转变——从“疾病导向”走向“个体导向”,这四类人群虽表现形式不同,但共同点在于无法被传统指南充分覆盖。医生需要识别“糖尿病谱系”背后的异质性,理解每例患者的代谢状态、器官功能、社会支持与生活目标,并据此制定动态调整的治疗方案。
2 comm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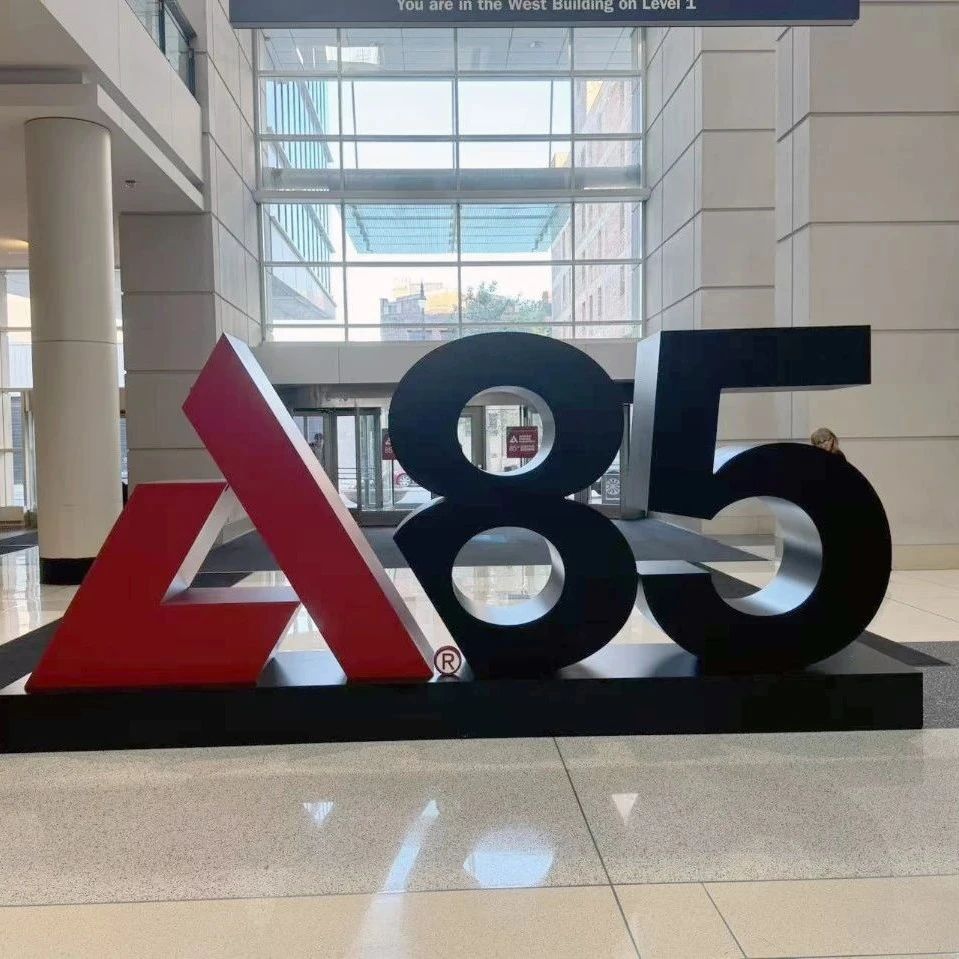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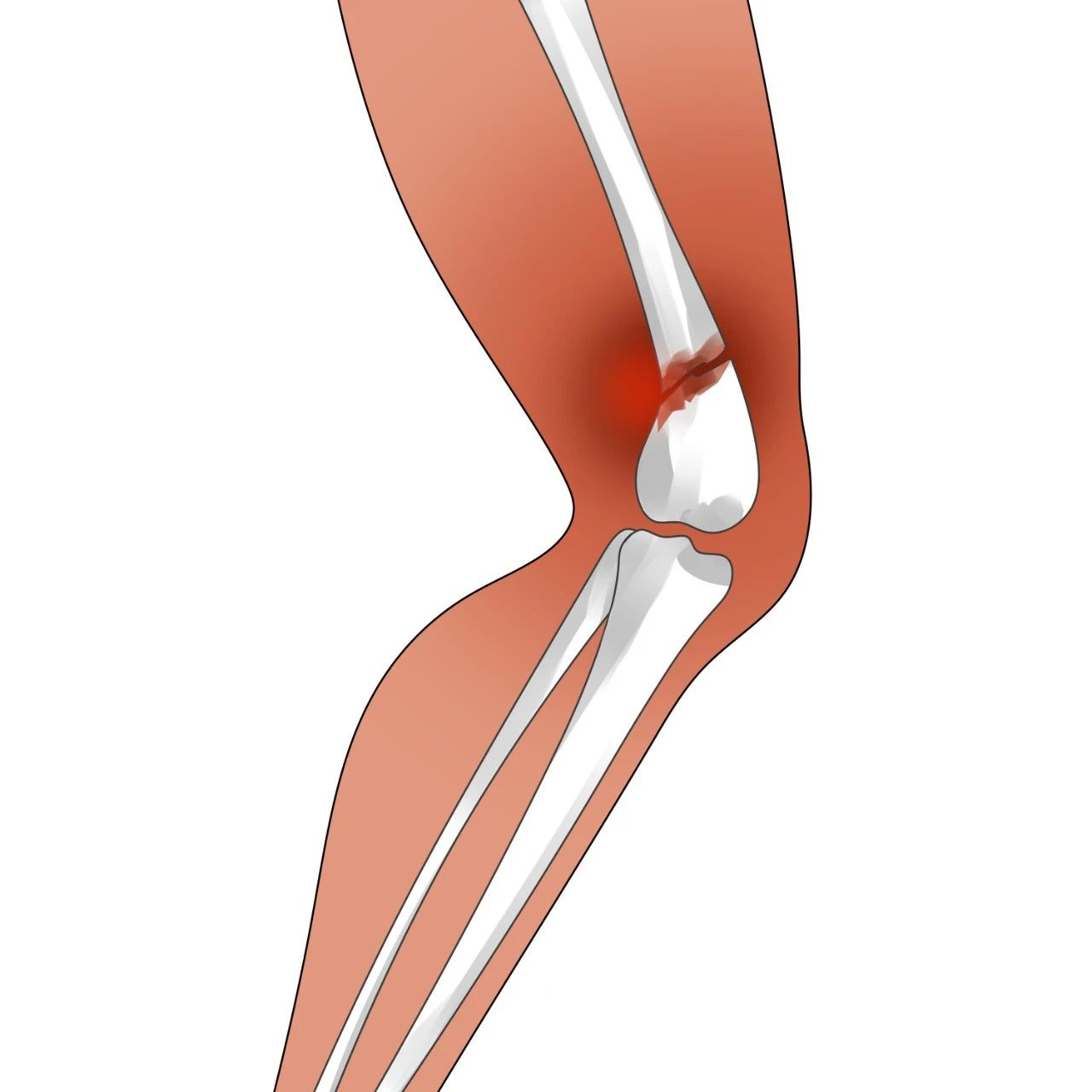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336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3361号
发布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