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糖尿病与痴呆的关联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议题,二者叠加不仅严重威胁患者生活质量,更带来沉重的社会医疗负担。在2025年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年会(EASD 2025)“糖尿病合并痴呆:希望之因还是担忧之由”专场中,三位专家分别从发病率攀升机制、降糖药的神经保护潜力及综合干预策略三个维度,深入解析糖尿病与痴呆的复杂关联,为临床实践与科学研究带来新启示。
糖尿病患者痴呆率为何攀升?
讲者:Thomas van Sloten(荷兰乌得勒支大学)
近年来,全球2型糖尿病(T2DM)患者痴呆发生率显著上升。数据显示[1],T2DM老年患者中每4人就有1人罹患痴呆,且糖尿病在痴呆发病中的“贡献权重”持续提升,已上升为痴呆风险第四大关联因素。
究其原因,主要由三大核心因素驱动:首先,老龄化与糖尿病患病率双重攀升,65岁以上老年群体糖尿病患病率增幅最显著,“老年+糖尿病”的叠加直接扩大高风险人群基数;其次,早期糖尿病的发病率增加,病程从过去约10年延长至15年以上,大脑暴露于高血糖、胰岛素抵抗等损伤因素的时间越久,痴呆风险越易累积;此外,糖尿病患者死亡率持续下降,原本因早亡未显现的痴呆风险得以充分暴露[2,3]。
风险因素层面,糖尿病发病年龄是关键调节器——中年(≤60岁)发病者的痴呆风险显著高于老年发病者;中年肥胖与糖尿病形成“风险叠加”,通过加重胰岛素抵抗、激活慢性炎症,共同损伤脑血管与神经元;吸烟、缺乏运动、高糖高脂饮食、高血压、低教育水平等共享风险因素,也会通过血管损伤、氧化应激等共同病理机制加剧认知损伤。
值得关注的是,1型糖尿病(T1DM)患者同样面临痴呆风险,其全因痴呆风险显著高于普通人群,提示长期血糖异常会对认知功能造成持续性损伤。应对策略核心在于“综合风险控制”:研究证实,当糖尿病患者同时实现HbA1c、BMI、血压达标,且不吸烟、保持健康饮食与规律运动(每周≥150分钟)等5~7项指标控制目标时,痴呆风险可接近无糖尿病人群,凸显“多维度管理”的重要性。目前,学界已呼吁将研究视角从“短期血糖控制”转向“终身健康视角”,并推动将“痴呆”纳入糖尿病治疗临床试验的核心结局指标。
糖尿病与痴呆:风险机制与干预策略
讲者:Gill Livingston(伦敦大学)
基于《柳叶刀》2024年痴呆委员会报告[4],糖尿病被明确列为可干预的关键风险因素。目前,全球痴呆患者超5700万,2050年将增至三倍,但高收入国家20年内特定年龄发病率的下降(如在美国≥65岁人群中,从2000年11.6%降至2012年8.8%,降幅约为25%),证实了痴呆可被预防。
研究显示,14项可改变风险因素占全球痴呆病例的45%,其中糖尿病加权人群归因分数(PAF)为2.5%。糖尿病使痴呆风险升高60~70%,且病程越长、发病年龄越早风险越高(每早5年发病风险增24%)。目前,痴呆预防的核心在于健康生活方式——不吸烟、适度饮酒、规律运动等可使糖尿病患者痴呆风险降低54%(HR=0.46),12年绝对风险从5.2%降至1.7%。病理机制聚焦胰岛素抵抗引发的脑胰岛素信号减弱,导致Aβ沉积、Tau过度磷酸化及微血管病变。
此外,降糖药物效也存在显著差异,一项RCT研究显示,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可降低痴呆风险53%(RR=0.47);而观察性研究发现,格列酮类可降低22%(RR=0.78);而二甲双胍效果存争议(RR=0.94),磺脲类和胰岛素甚至可能增加风险(RR=1.09)。
痴呆的预防从个体和社会两方面着手。个体层面,应改善生活方式并优先使用有痴呆预防效果的GLP-1RA类药物。社会层面,要突破个体责任限制,通过政策优化贫困群体生活环境,推动公平干预。最终目标是借助药物研发和社会政策,实现“疾病压缩”,让疾病高发期推迟至生命晚期,延长健康生活时长。
降糖药物能否用于治疗痴呆?
讲者:Alice YY Cheng(多伦多大学)
糖尿病与痴呆的关联核心在于高胰岛素血症引发的脑胰岛素抵抗。病理机制上,血脑屏障(BBB)功能障碍导致胰岛素转运体下调、Aβ寡聚体使胰岛素受体丢失,削弱脑内胰岛素信号传导;同时触发多重病理级联反应,包括高血糖神经毒性、晚期糖基化终产物(AGEs)积累、内质网/氧化应激,以及IL-1β、IL-6、TNF-α释放激活小胶质细胞,最终导致Aβ沉积、Tau过度磷酸化、线粒体功能障碍、多巴胺耗竭[5]。
目前,有三类降糖药物在痴呆风险干预中潜力凸显:
鼻内胰岛素(INI):Meta分析纳入12项阿尔茨海默病(AD)/轻度认知障碍(MCI)患者研究,显示INI显著改善认知,但异质性高,需优化给药方案。
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因脑区(海马体、下丘脑等)分布SGLT1/2,且具有抑制NLRP3炎症小体、促进M2巨噬细胞极化、激活SIRT/AMPK通路等多效性保护作用,可减轻Aβ/Tau病理。此外,韩国一项纳入358 862例患者大型队列研究证实,SGLT2i降低阿尔茨海默病风险31%(aHR=0.69)、血管性痴呆风险21%(aHR=0.79)。
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能修复胰岛素信号(增加IR/IGF-1R表达,抑制神经炎症与氧化应激),且艾塞那肽、利西拉肽可穿透BBB,长效制剂(如司美格鲁肽)通过室周器官入脑[6]。瑞典队列(n=88 417)显示,GLP-1RA较磺脲类降低痴呆风险31%(HR=0.69)[7];REWIND试验事后分析表明,度拉糖肽降低认知障碍风险14%(HR=0.86,P=0.0018)[8]。
未来研究将从风险干预转向疾病修饰治疗。当前,EVOKE/EVOKE+试验(3808例受试者)正评估司美格鲁肽对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疗效,主要终点为CDR-SB,预计2026年完成[9];同时,也在探索鼻内胰岛素联合口服司美格鲁肽治疗代谢综合征高危人群的联合疗法;此外,双受体激动剂(如GLP-1/GIP双激动剂),可同时调节神经炎症和能量代谢,未来是否也能展现出成为疾病修饰治疗的潜力?
结语
EASD 2025的糖尿病与痴呆专场报告,揭示了疾病关联的严峻现实与防控曙光。糖尿病患者痴呆率攀升源于老龄化、病程延长等压力,中年发病与肥胖叠加风险,凸显终身综合管理的紧迫性。病理机制聚焦脑胰岛素抵抗,而GLP-1RA、SGLT2i药物在降低痴呆风险中展现突破性潜力。健康生活方式可使患者痴呆风险降低54%,而全球45%病例可通过干预14项风险因素预防。未来需构建“个体-医疗-社会”三重防线——优化生活方式、精准用药、推动健康公平政策,最终实现“疾病压缩”,将患病集中于生命晚期。
参考文献
1.van Sloten TT, et al.Lancet Diabetes Endocrinol. 2024;12(8):510-513.
2.Tomic D, et al. Nat Rev Endocrinol. 2022;18(9):525-539.
3.Barbiellini Amidei C, et al. JAMA. 2021;325(16):1640-1649.
4.Livingston G, et al. Lancet. 2024;404(10452):572-628.
5.Monney M, et al. Diabetes Metab. 2023;49(5):101470.
6.Vear A, et al. Nat Metab. 2025;7(4):679-696.
7.Tang B, et al. EClinicalMedicine. 2024;73:102689.
8.Cukierman-Yaffe T, et al. Lancet Neurol. 2020;19(7):582-590.
9.Cummings JL, et al. Alzheimers Dement (N Y). 2025;11(2):e70098.
2 comments
糖尿病与痴呆的关联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议题,二者叠加不仅严重威胁患者生活质量,更带来沉重的社会医疗负担。在2025年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年会(EASD 2025)“糖尿病合并痴呆:希望之因还是担忧之由”专场中,三位专家分别从发病率攀升机制、降糖药的神经保护潜力及综合干预策略三个维度,深入解析糖尿病与痴呆的复杂关联,为临床实践与科学研究带来新启示。
糖尿病患者痴呆率为何攀升?
讲者:Thomas van Sloten(荷兰乌得勒支大学)
近年来,全球2型糖尿病(T2DM)患者痴呆发生率显著上升。数据显示[1],T2DM老年患者中每4人就有1人罹患痴呆,且糖尿病在痴呆发病中的“贡献权重”持续提升,已上升为痴呆风险第四大关联因素。
究其原因,主要由三大核心因素驱动:首先,老龄化与糖尿病患病率双重攀升,65岁以上老年群体糖尿病患病率增幅最显著,“老年+糖尿病”的叠加直接扩大高风险人群基数;其次,早期糖尿病的发病率增加,病程从过去约10年延长至15年以上,大脑暴露于高血糖、胰岛素抵抗等损伤因素的时间越久,痴呆风险越易累积;此外,糖尿病患者死亡率持续下降,原本因早亡未显现的痴呆风险得以充分暴露[2,3]。
风险因素层面,糖尿病发病年龄是关键调节器——中年(≤60岁)发病者的痴呆风险显著高于老年发病者;中年肥胖与糖尿病形成“风险叠加”,通过加重胰岛素抵抗、激活慢性炎症,共同损伤脑血管与神经元;吸烟、缺乏运动、高糖高脂饮食、高血压、低教育水平等共享风险因素,也会通过血管损伤、氧化应激等共同病理机制加剧认知损伤。
值得关注的是,1型糖尿病(T1DM)患者同样面临痴呆风险,其全因痴呆风险显著高于普通人群,提示长期血糖异常会对认知功能造成持续性损伤。应对策略核心在于“综合风险控制”:研究证实,当糖尿病患者同时实现HbA1c、BMI、血压达标,且不吸烟、保持健康饮食与规律运动(每周≥150分钟)等5~7项指标控制目标时,痴呆风险可接近无糖尿病人群,凸显“多维度管理”的重要性。目前,学界已呼吁将研究视角从“短期血糖控制”转向“终身健康视角”,并推动将“痴呆”纳入糖尿病治疗临床试验的核心结局指标。
糖尿病与痴呆:风险机制与干预策略
讲者:Gill Livingston(伦敦大学)
基于《柳叶刀》2024年痴呆委员会报告[4],糖尿病被明确列为可干预的关键风险因素。目前,全球痴呆患者超5700万,2050年将增至三倍,但高收入国家20年内特定年龄发病率的下降(如在美国≥65岁人群中,从2000年11.6%降至2012年8.8%,降幅约为25%),证实了痴呆可被预防。
研究显示,14项可改变风险因素占全球痴呆病例的45%,其中糖尿病加权人群归因分数(PAF)为2.5%。糖尿病使痴呆风险升高60~70%,且病程越长、发病年龄越早风险越高(每早5年发病风险增24%)。目前,痴呆预防的核心在于健康生活方式——不吸烟、适度饮酒、规律运动等可使糖尿病患者痴呆风险降低54%(HR=0.46),12年绝对风险从5.2%降至1.7%。病理机制聚焦胰岛素抵抗引发的脑胰岛素信号减弱,导致Aβ沉积、Tau过度磷酸化及微血管病变。
此外,降糖药物效也存在显著差异,一项RCT研究显示,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可降低痴呆风险53%(RR=0.47);而观察性研究发现,格列酮类可降低22%(RR=0.78);而二甲双胍效果存争议(RR=0.94),磺脲类和胰岛素甚至可能增加风险(RR=1.09)。
痴呆的预防从个体和社会两方面着手。个体层面,应改善生活方式并优先使用有痴呆预防效果的GLP-1RA类药物。社会层面,要突破个体责任限制,通过政策优化贫困群体生活环境,推动公平干预。最终目标是借助药物研发和社会政策,实现“疾病压缩”,让疾病高发期推迟至生命晚期,延长健康生活时长。
降糖药物能否用于治疗痴呆?
讲者:Alice YY Cheng(多伦多大学)
糖尿病与痴呆的关联核心在于高胰岛素血症引发的脑胰岛素抵抗。病理机制上,血脑屏障(BBB)功能障碍导致胰岛素转运体下调、Aβ寡聚体使胰岛素受体丢失,削弱脑内胰岛素信号传导;同时触发多重病理级联反应,包括高血糖神经毒性、晚期糖基化终产物(AGEs)积累、内质网/氧化应激,以及IL-1β、IL-6、TNF-α释放激活小胶质细胞,最终导致Aβ沉积、Tau过度磷酸化、线粒体功能障碍、多巴胺耗竭[5]。
目前,有三类降糖药物在痴呆风险干预中潜力凸显:
鼻内胰岛素(INI):Meta分析纳入12项阿尔茨海默病(AD)/轻度认知障碍(MCI)患者研究,显示INI显著改善认知,但异质性高,需优化给药方案。
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因脑区(海马体、下丘脑等)分布SGLT1/2,且具有抑制NLRP3炎症小体、促进M2巨噬细胞极化、激活SIRT/AMPK通路等多效性保护作用,可减轻Aβ/Tau病理。此外,韩国一项纳入358 862例患者大型队列研究证实,SGLT2i降低阿尔茨海默病风险31%(aHR=0.69)、血管性痴呆风险21%(aHR=0.79)。
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能修复胰岛素信号(增加IR/IGF-1R表达,抑制神经炎症与氧化应激),且艾塞那肽、利西拉肽可穿透BBB,长效制剂(如司美格鲁肽)通过室周器官入脑[6]。瑞典队列(n=88 417)显示,GLP-1RA较磺脲类降低痴呆风险31%(HR=0.69)[7];REWIND试验事后分析表明,度拉糖肽降低认知障碍风险14%(HR=0.86,P=0.0018)[8]。
未来研究将从风险干预转向疾病修饰治疗。当前,EVOKE/EVOKE+试验(3808例受试者)正评估司美格鲁肽对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疗效,主要终点为CDR-SB,预计2026年完成[9];同时,也在探索鼻内胰岛素联合口服司美格鲁肽治疗代谢综合征高危人群的联合疗法;此外,双受体激动剂(如GLP-1/GIP双激动剂),可同时调节神经炎症和能量代谢,未来是否也能展现出成为疾病修饰治疗的潜力?
结语
EASD 2025的糖尿病与痴呆专场报告,揭示了疾病关联的严峻现实与防控曙光。糖尿病患者痴呆率攀升源于老龄化、病程延长等压力,中年发病与肥胖叠加风险,凸显终身综合管理的紧迫性。病理机制聚焦脑胰岛素抵抗,而GLP-1RA、SGLT2i药物在降低痴呆风险中展现突破性潜力。健康生活方式可使患者痴呆风险降低54%,而全球45%病例可通过干预14项风险因素预防。未来需构建“个体-医疗-社会”三重防线——优化生活方式、精准用药、推动健康公平政策,最终实现“疾病压缩”,将患病集中于生命晚期。
参考文献
1.van Sloten TT, et al.Lancet Diabetes Endocrinol. 2024;12(8):510-513.
2.Tomic D, et al. Nat Rev Endocrinol. 2022;18(9):525-539.
3.Barbiellini Amidei C, et al. JAMA. 2021;325(16):1640-1649.
4.Livingston G, et al. Lancet. 2024;404(10452):572-628.
5.Monney M, et al. Diabetes Metab. 2023;49(5):101470.
6.Vear A, et al. Nat Metab. 2025;7(4):679-696.
7.Tang B, et al. EClinicalMedicine. 2024;73:102689.
8.Cukierman-Yaffe T, et al. Lancet Neurol. 2020;19(7):582-590.
9.Cummings JL, et al. Alzheimers Dement (N Y). 2025;11(2):e70098.
2 comm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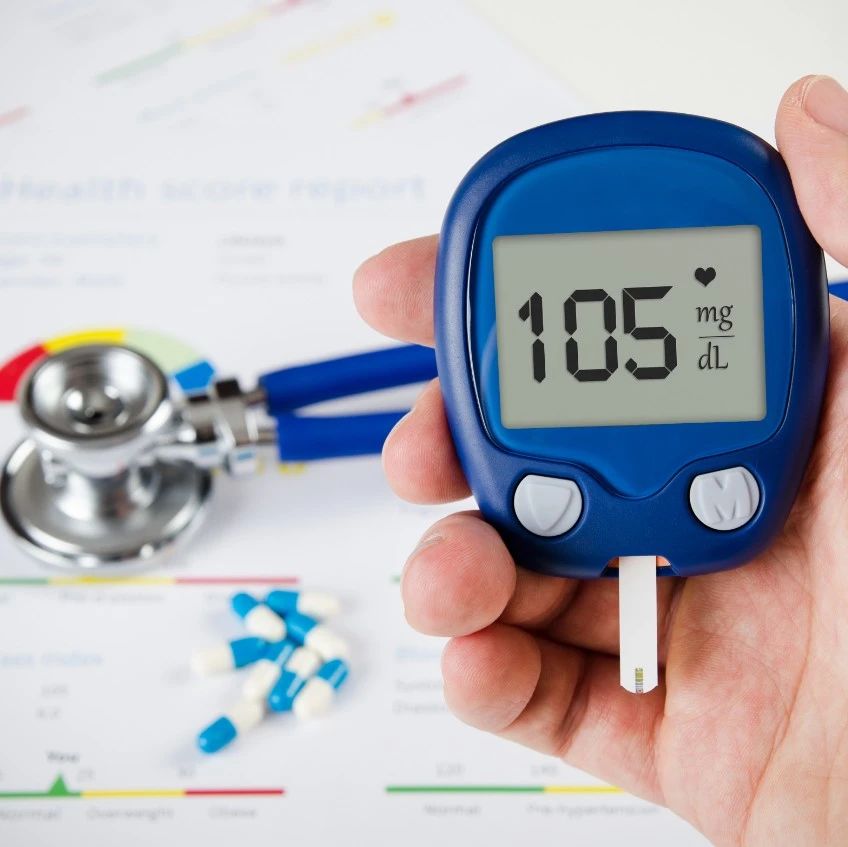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336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3361号
发布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