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5月17~19日,2024北大糖尿病论坛(PUDF 2024)在北京会议中心盛大召开。本届论坛以“心肾代谢”为主题,聚焦心血管-肾脏-代谢(CKM)综合征的病因、发病机制、风险因素、筛查、评估及防治管理策略等方面,为参会者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学术盛宴。正所谓“大医治未病”,CKM综合征的预防至关重要!如何分析CKM综合征的社会决定因素?如何在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降低CKM综合征风险?会议期间,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马军教授以“心血管-肾脏-代谢综合征的社会决定因素”为题进行了翔实报告,现整理精粹如下,以飨读者。

近几十年来,全球范围内儿童青少年正在由低体重向超重与肥胖快速转变,这一趋势在我国尤为明显。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对1985至2019年(1985、1995、2000、2005、2010、2014、2019年的样本量分别为409 945、204 931、209 209、234 420、215 317、214 353、212 711例)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结果显示,近35年来我国7~18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检出率持续增长,这一变化趋势和特点不容乐观[1]。
2019年中国7~18岁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总检出率为23.4%(49 828/212 711),超重和肥胖检出率分别为13.9%(29 488/212 711)和9.6%(20 340/212 711)。这一数据表明我国儿童青少年的营养状态已从营养不良转向营养过剩。亚组分析显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亦或城市、乡村,7~18岁儿童青少年均呈现消瘦快速转为超重或肥胖的趋势[2]。超重与肥胖检出率随年龄的变化趋势不同,超重检出率在7~18岁年龄段之间变化较为稳定,而肥胖检出率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亚组分析显示在城市男生、城市女生、乡村男生和乡村女生超重与肥胖检出率呈现相同的趋势(图1)。

多项式回归函数预测模型显示(R2均高于99.9%),7~18岁学生超重肥胖及肥胖检出率将由2019年的23.4%和9.6%增长至2030年的32.7%和15.1%。未来乡村男生和乡村女生的超重肥胖检出率将全面超过城市,预计2034年乡村女生超重与肥胖检出率将超过城市男生(检出率为34.7%),2047年乡村女生肥胖检出率将超过城市男生(24.6%)(图2)。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儿童青少年膳食结构及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饮食模式从食物短缺、单一营养素摄入向以高脂肪、高热量和精制碳水化合物为主的饮食模式转变。与此同时,我国儿童青少年课业负担重、电子产品视屏时间长、身体活动不足现象广泛存在[3-6]。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直接导致儿童青少年的超重肥胖率快速上升,健康问题日益严重。
有研究显示,我国汉族男生首次遗精年龄提前,每10年大约提前4个月;汉族女生首次月经初潮年龄提前,每10年大约提前4.5个月,儿童青少年肥胖流行与青春期发育提前有较强相关性[7,8]。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剧了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快速上升,当人均GDP达到$4000、恩格尔系数低于50%时,农村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风险增加[9,10]。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儿童青少年时期的超重与肥胖可以持续到成年,且与整个生命过程的不良健康结局相关,大幅度增加了成年期患心血管疾病、血脂异常、糖尿病、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肌肉骨骼疾病和癌症等疾病的负担,并可能带来不良的心理健康状态和较低教育水平[11-15]。
在超重、肥胖儿童中可检测出早期心血管结构和功能损伤。血管损伤表现为:结构损害——血管内中膜厚度(cIMT)升高;硬度增加——脉搏传导速度(PWV)升高;内皮功能紊乱——血流介导的血管舒张功能(FMD)降低。心脏损伤表现为:结构损害——左心室质量(LVM)、左心室质量指数(LVMI)、相对室壁厚度(RWT)升高,出现左心室肥厚(LVH);功能损害——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二尖瓣口舒张早期血流峰值速度与二尖瓣环峰值速度比值(E/E′)降低[16-18]。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存在的“轨迹现象”将会增加成年期心血管疾病风险[19,20]。
同样,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会导致肾损伤相关病理变化,进而增加成年早期慢性肾脏疾病的风险[21,22]。不仅如此,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可表现为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甘油三酯升高、血压偏高、空腹血糖偏高等,进而导致总体代谢综合征患病率升高[23-25]。
儿童青少年时期是全生命周期中关系身心健康发展的关键时期,儿童青少年肥胖不仅是单纯的独立疾病,并会显著增加成年期CKM综合征风险。因而,肥胖的防治越早,获益越大。做好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防控的基础是梳理当前政策行动与儿童青少年健康问题、健康风险和健康决定因素的需求。继而推动以政府为主导的跨国家卫健委、疾控、教育和社区等多部门的协作策略,以及创建以儿童青少年健康为中心的多病共防干预体系[26]。
总体来说,当前工作的首要任务是要以提高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和素养为核心,以社会生态理论为理论基础,在学生、家庭和学校三个层面密切协作、共同干预,同时在互联网医疗和大数据管理快速发展的机遇中,基于云服务平台,利用手机APP等工具促进各方联动,从而有效遏制肥胖的流行(图3)。

美国心脏协会(AHA)主席建议指出,CKM综合征应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从生命早期即开始进行筛查。在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发生率持续攀升的态势下,亟待统筹各方资源,制定、调整并落实儿童肥胖防控政策和措施,遏制我国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的高速增长势头,进而降低成年期CKM综合征的风险。
参考文献
1.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 2019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R].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2.
2.Dong Y, et al. Lancet Diabetes Endocrinol. 2019 Apr;7(4): 288-299.
3.Fu JL, BY Wang. Chin J Epidemiol, 2007. 28(3): 297-300.
4.Dong, Y, et al. Lancet Child Adolesc Health, 2019. 3(12):. 871-880.
5.Popkin, BM. and P. Gordon-Larsen. Int J Obes Relat Metab Disord, 2004. 28 Suppl 3: S2-9.
6.王烁,等.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17. 51(4): 300-305.
7.Journal of Pediatrics, 2014.
8.Pediatric Obesity, 2016.
9.Lancet Diabetes & Endocrinology, 2019.
10.Public Health Nutrition, 2019.
11.Twig, G, et al. N Engl J Med, 2016. 374(25): 2430-40.
12.Batty, G.D, et al. Am J Epidemiol, 2015. 182(9): 775-80.
13.Cuspidi, C, et al. J Hypertens, 2014. 32(1): 16-25.
14.Caird, J, et al. Health Education Journal, 2014. 73(5): 497-521.
15.Quek, YH. et al. Obes Rev, 2017. 18(7): 742-754.
16.Eur Heart J. 2015 Jun 7;36(22): 1371-6.
17.J Am Coll Cardiol. 2012 Dec 25; 60(25): 2643-50.
18.Diabetes Care. 2019 Jan; 42(1): 119-125.
19.Obes Rev. 2021 Mar;22(3): e13138.
20.Obes Rev. 2024 Apr;25(4): e13695.
21.Curr Obes Rep. 2023 Sep;12(3): 332-344.
22.JAMA Pediatr. 2024 Feb 1;178(2): 142-150.
23.J Pediatr. 2013 Jul;163(1): 137-42.
24.Circulation. 2004 Oct 19;110(16):2494-7.
25.N Engl J Med. 2004 Jun 3;350(23):2362-74.
26.Chen T, et al. Lancet, 2024.
2 comments
5月17~19日,2024北大糖尿病论坛(PUDF 2024)在北京会议中心盛大召开。本届论坛以“心肾代谢”为主题,聚焦心血管-肾脏-代谢(CKM)综合征的病因、发病机制、风险因素、筛查、评估及防治管理策略等方面,为参会者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学术盛宴。正所谓“大医治未病”,CKM综合征的预防至关重要!如何分析CKM综合征的社会决定因素?如何在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降低CKM综合征风险?会议期间,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马军教授以“心血管-肾脏-代谢综合征的社会决定因素”为题进行了翔实报告,现整理精粹如下,以飨读者。

直击现状:超重与肥胖问题日益严峻
近几十年来,全球范围内儿童青少年正在由低体重向超重与肥胖快速转变,这一趋势在我国尤为明显。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对1985至2019年(1985、1995、2000、2005、2010、2014、2019年的样本量分别为409 945、204 931、209 209、234 420、215 317、214 353、212 711例)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结果显示,近35年来我国7~18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检出率持续增长,这一变化趋势和特点不容乐观[1]。
2019年中国7~18岁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总检出率为23.4%(49 828/212 711),超重和肥胖检出率分别为13.9%(29 488/212 711)和9.6%(20 340/212 711)。这一数据表明我国儿童青少年的营养状态已从营养不良转向营养过剩。亚组分析显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亦或城市、乡村,7~18岁儿童青少年均呈现消瘦快速转为超重或肥胖的趋势[2]。超重与肥胖检出率随年龄的变化趋势不同,超重检出率在7~18岁年龄段之间变化较为稳定,而肥胖检出率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亚组分析显示在城市男生、城市女生、乡村男生和乡村女生超重与肥胖检出率呈现相同的趋势(图1)。

图1. 2019年中国7~18岁城乡男女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检出率随年龄变化情况
多项式回归函数预测模型显示(R2均高于99.9%),7~18岁学生超重肥胖及肥胖检出率将由2019年的23.4%和9.6%增长至2030年的32.7%和15.1%。未来乡村男生和乡村女生的超重肥胖检出率将全面超过城市,预计2034年乡村女生超重与肥胖检出率将超过城市男生(检出率为34.7%),2047年乡村女生肥胖检出率将超过城市男生(24.6%)(图2)。

图2. 1985年至2019年中国7~18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和仅肥胖检出率和预测
抽丝剥茧:剖析社会经济因素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儿童青少年膳食结构及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饮食模式从食物短缺、单一营养素摄入向以高脂肪、高热量和精制碳水化合物为主的饮食模式转变。与此同时,我国儿童青少年课业负担重、电子产品视屏时间长、身体活动不足现象广泛存在[3-6]。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直接导致儿童青少年的超重肥胖率快速上升,健康问题日益严重。
有研究显示,我国汉族男生首次遗精年龄提前,每10年大约提前4个月;汉族女生首次月经初潮年龄提前,每10年大约提前4.5个月,儿童青少年肥胖流行与青春期发育提前有较强相关性[7,8]。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剧了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快速上升,当人均GDP达到$4000、恩格尔系数低于50%时,农村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风险增加[9,10]。
危害深远:增加成年期CKM综合征风险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儿童青少年时期的超重与肥胖可以持续到成年,且与整个生命过程的不良健康结局相关,大幅度增加了成年期患心血管疾病、血脂异常、糖尿病、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肌肉骨骼疾病和癌症等疾病的负担,并可能带来不良的心理健康状态和较低教育水平[11-15]。
在超重、肥胖儿童中可检测出早期心血管结构和功能损伤。血管损伤表现为:结构损害——血管内中膜厚度(cIMT)升高;硬度增加——脉搏传导速度(PWV)升高;内皮功能紊乱——血流介导的血管舒张功能(FMD)降低。心脏损伤表现为:结构损害——左心室质量(LVM)、左心室质量指数(LVMI)、相对室壁厚度(RWT)升高,出现左心室肥厚(LVH);功能损害——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二尖瓣口舒张早期血流峰值速度与二尖瓣环峰值速度比值(E/E′)降低[16-18]。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存在的“轨迹现象”将会增加成年期心血管疾病风险[19,20]。
同样,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会导致肾损伤相关病理变化,进而增加成年早期慢性肾脏疾病的风险[21,22]。不仅如此,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可表现为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甘油三酯升高、血压偏高、空腹血糖偏高等,进而导致总体代谢综合征患病率升高[23-25]。
防控策略:多方联动,共同干预
儿童青少年时期是全生命周期中关系身心健康发展的关键时期,儿童青少年肥胖不仅是单纯的独立疾病,并会显著增加成年期CKM综合征风险。因而,肥胖的防治越早,获益越大。做好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防控的基础是梳理当前政策行动与儿童青少年健康问题、健康风险和健康决定因素的需求。继而推动以政府为主导的跨国家卫健委、疾控、教育和社区等多部门的协作策略,以及创建以儿童青少年健康为中心的多病共防干预体系[26]。
总体来说,当前工作的首要任务是要以提高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和素养为核心,以社会生态理论为理论基础,在学生、家庭和学校三个层面密切协作、共同干预,同时在互联网医疗和大数据管理快速发展的机遇中,基于云服务平台,利用手机APP等工具促进各方联动,从而有效遏制肥胖的流行(图3)。

图3. 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防控策略
结语
美国心脏协会(AHA)主席建议指出,CKM综合征应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从生命早期即开始进行筛查。在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发生率持续攀升的态势下,亟待统筹各方资源,制定、调整并落实儿童肥胖防控政策和措施,遏制我国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的高速增长势头,进而降低成年期CKM综合征的风险。
参考文献
1.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 2019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R].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2.
2.Dong Y, et al. Lancet Diabetes Endocrinol. 2019 Apr;7(4): 288-299.
3.Fu JL, BY Wang. Chin J Epidemiol, 2007. 28(3): 297-300.
4.Dong, Y, et al. Lancet Child Adolesc Health, 2019. 3(12):. 871-880.
5.Popkin, BM. and P. Gordon-Larsen. Int J Obes Relat Metab Disord, 2004. 28 Suppl 3: S2-9.
6.王烁,等.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17. 51(4): 300-305.
7.Journal of Pediatrics, 2014.
8.Pediatric Obesity, 2016.
9.Lancet Diabetes & Endocrinology, 2019.
10.Public Health Nutrition, 2019.
11.Twig, G, et al. N Engl J Med, 2016. 374(25): 2430-40.
12.Batty, G.D, et al. Am J Epidemiol, 2015. 182(9): 775-80.
13.Cuspidi, C, et al. J Hypertens, 2014. 32(1): 16-25.
14.Caird, J, et al. Health Education Journal, 2014. 73(5): 497-521.
15.Quek, YH. et al. Obes Rev, 2017. 18(7): 742-754.
16.Eur Heart J. 2015 Jun 7;36(22): 1371-6.
17.J Am Coll Cardiol. 2012 Dec 25; 60(25): 2643-50.
18.Diabetes Care. 2019 Jan; 42(1): 119-125.
19.Obes Rev. 2021 Mar;22(3): e13138.
20.Obes Rev. 2024 Apr;25(4): e13695.
21.Curr Obes Rep. 2023 Sep;12(3): 332-344.
22.JAMA Pediatr. 2024 Feb 1;178(2): 142-150.
23.J Pediatr. 2013 Jul;163(1): 137-42.
24.Circulation. 2004 Oct 19;110(16):2494-7.
25.N Engl J Med. 2004 Jun 3;350(23):2362-74.
26.Chen T, et al. Lancet, 2024.
2 comm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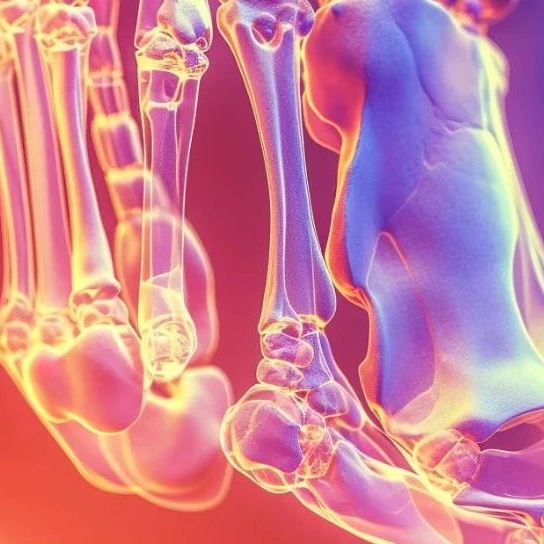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336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3361号
发布留言